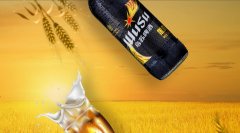中國人購物置地的報(bào)道越來越多地出現(xiàn)在西方媒體中,但字里行間滲透著感慨、驚詫、懷疑甚或不解的情緒。外國社會(huì)對(duì)中國“買家”始終有一種微妙的態(tài)度。
和倫敦有著1小時(shí)火車距離的小鎮(zhèn)Bicester,有著英國乃至歐洲聞名的“Outlet Store”(“暢貨中心”,指在大都市郊外開設(shè)的大賣場(chǎng),以極為低廉的價(jià)格出售過季的名牌貨)。
這種賣場(chǎng)因其價(jià)廉物美而受到各國旅游者和中產(chǎn)人士的喜愛。但近兩年來,對(duì)Bicester的抱怨開始增加,“怎么現(xiàn)在這里的折扣越來越少,價(jià)格越來越不劃算了?”在英國的女留學(xué)生王小慧告訴《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人周刊》。她曾是這里的常客,不過這兩年她很少光顧,因?yàn)椴惶珓澦懔恕?/p>
中國人購物置地的報(bào)道越來越多地出現(xiàn)在西方媒體中,但字里行間滲透著感慨、驚詫、懷疑甚或不解的情緒。
相似的一幕,其實(shí)曾在上世紀(jì)80年代出現(xiàn)過,當(dāng)時(shí)的日本“幾乎買下了半個(gè)美國”。
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(xué)生和旅行團(tuán)到發(fā)達(dá)國家“掃貨”,使得當(dāng)?shù)厣碳乙辉偬岣邇r(jià)格。幾乎所有名牌專賣店,如巴寶莉(Burberry)、古馳(Gucci)等都增加了華人員工為中國客人服務(wù),“您可以使用中文購物”的告示格外醒目。Burberry在倫敦銷售額的30%來自中國游客,而中國游客買走了歐洲Gucci22%的銷售額。
“北京鎊”(指中國人在英國花的錢)已經(jīng)在英國成為一個(gè)新名詞。2009年,中國游客的開銷比前一年增長了3-4倍。
位于東京銀座著名的三越百貨店內(nèi),售貨小姐用中文和客人交流的情形甚為平常。付款處貼著“我們歡迎使用銀聯(lián)”的告示,上了年紀(jì)的日本管理人員站在門口,給魚貫而入的中國游客90度鞠躬。1月24日的日本《朝日新聞》以《期待中國人的錢包》為題,報(bào)道了日本靜岡縣為迎接來自春節(jié)假期的中國游客而做的種種努力,包括提供中文說明、中文導(dǎo)購和相關(guān)金融服務(wù)。
即使在中國特別行政區(qū)香港,來自大陸的購物潮也讓商品價(jià)格一再上提。“圣誕期間的折扣少得可憐,有些根本沒有,以往有很多兩三折的商品。”在紐約華人街日?qǐng)?bào)工作的小王和香港《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人周刊》聊起香港目前購物現(xiàn)狀,“現(xiàn)在去香港購物的人真的太多了,過個(gè)關(guān)都要好幾個(gè)小時(shí)。”
這些,僅僅是“中國人購物狂潮”的縮影。事實(shí)上,從倫敦的哈羅百貨,到巴黎的老佛爺百貨到米蘭附近的一些名牌工廠店,沒有人能預(yù)測(cè)中國買家的上限在哪里。
據(jù)全球報(bào)告組織統(tǒng)計(jì),中國已經(jīng)超越了美國,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購買國。
圣誕節(jié)前,57歲的香港房地產(chǎn)大亨劉鑾雄(身家25億英鎊)花3300萬英鎊買下了倫敦高檔住宅區(qū)一幢6層豪宅。英國《每日郵報(bào)》指出,中國買家是目前倫敦最活躍的海外投資者。很多中國大陸人在倫敦物色房子(預(yù)算800萬-1700萬英鎊)。“如果這些中國人不買房,就會(huì)買公司,買很多公司。”
是的,中國企業(yè)的海外收購和擴(kuò)張?jiān)谕竭M(jìn)行。從聯(lián)想收購IBM的Thinkpad業(yè)務(wù)到吉利整體收購沃爾沃,到最近的中石油收購歐洲的煉油廠和工商銀行收購美國東亞銀行。
國際社會(huì)和輿論已經(jīng)從一開始的驚詫、議論紛紛到現(xiàn)在的習(xí)以為常。媒體的觀點(diǎn)已經(jīng)從“中國人會(huì)來收購嗎?”發(fā)展到“中國人會(huì)出價(jià)多少?”
海外采購的第三個(gè)層次就是政府采購。“有人開玩笑說是‘坐著飛機(jī)吃大豆’(兩種我國政府近年來最常采購的商品)。”哥倫比亞商學(xué)院威廉姆斯教授接受到媒體采訪時(shí)形容中國的政府采購,“他們長期以來為了在短期內(nèi)平衡國際收支,做了很多這樣的采購。”
“去年9月份我去了中國,感受很深。中國人,特別是富有階層的中國人在美國非常有錢,但是他們對(duì)奢侈品的追求并不讓我覺得舒服。”威廉姆斯感慨,“過度的追求奢侈品既不利于國家持續(xù)發(fā)展動(dòng)力的提高,在西方人眼里,更多是暴發(fā)戶的形象。”
外國社會(huì)對(duì)中國“買家”始終有一種微妙的態(tài)度。中國客人由中國員工接待,外籍員工往往冷冷地在一旁看著,似乎在看著來自另一個(gè)世界的人。小偷們也總喜歡盯著中國人,因?yàn)槎贾馈爸袊擞绣X,且現(xiàn)金多”。
倫敦的酒商也對(duì)中國人有兩種印象。首先,錢不是問題。蘇富比拍賣行不久前宣布,一瓶1869年的“拉菲”以超過13萬英鎊的價(jià)格被―位中國買家買走。“順便說一句,買那瓶酒是為了喝,而不是藏在酒窖里。”近一年來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人們幾乎肯出任何價(jià)錢買酒,”佳士得拍賣行的酒類拍品負(fù)責(zé)人戴維?埃爾斯伍德說:“這不是投資,而是無節(jié)制的消費(fèi)。”
其次,中國買家有他們自己的喝酒方式,而這種方式可能令傳統(tǒng)的品酒行家感到驚詫。即便是6000英鎊一瓶的1982年法國頂級(jí)紅葡萄酒,中國人也會(huì)端起酒杯一飲而盡。他們會(huì)干掉一整杯,甚至加入可口可樂,讓酒喝起來更甜。”《紐約每日電訊》報(bào)道。
出生在香港的倫敦理財(cái)師安迪?王說:“西方生活方式對(duì)大多數(shù)中國人都沒有吸引力。”他說: “他們絕不認(rèn)為乘坐豪華游艇遨游法國圣特羅佩灣有什么特別吸引人之處。”那他們做些什么?“哦,你知道,他們喜歡養(yǎng)鳥”。 安迪說,“還有書法、繪畫之類的事情。”
“中國有13億人,最富裕的人數(shù)即使很少也有6000多萬,就和歐洲一個(gè)國家總?cè)丝谝粯樱@當(dāng)然是一個(gè)很大的消費(fèi)人群。”威廉姆斯分析道,“但是從另一方面說,按照聯(lián)合國GDP3000-8000美元的標(biāo)準(zhǔn)劃分,中國剛剛邁入中等發(fā)達(dá)國家下限。在這種情況下,過度奢侈自然會(huì)引來非議。”
《紐約時(shí)報(bào)》在一篇名為《購物,中國,購物》的文章里也寫到:中國依然是一個(gè)相對(duì)貧窮的國家,他的人均GDP比泰國和秘魯都要低。在遠(yuǎn)離大城市的農(nóng)村里,許多人依然因?yàn)樨毨ЬS持著最低水平的物質(zhì)生活及放棄最基本的教育。
相對(duì)于個(gè)人的消費(fèi)購買來說,以企業(yè)和國家行為的海外購買因?yàn)闋砍哆M(jìn)更多的商業(yè)和政治因素,并不適合用簡(jiǎn)單的道德思維去剖析。
但是在客觀上,目前的中國企業(yè)還缺乏很經(jīng)典的海外收購的成功案例,我們總是能聽到不和諧的聲音。
歐盟委員會(huì)負(fù)責(zé)工業(yè)事務(wù)的副主席安東尼奧?塔亞尼(AntonioTajani)近期就發(fā)表言論要求:歐盟審查那些帶有“明顯威脅性的投資”。這被認(rèn)為直接指向來自中國一家不明企業(yè)對(duì)一家荷蘭光纖企業(yè)的失敗收購。而另一名歐盟高級(jí)官員,貿(mào)易專員古赫特(Karel DeGucht),近期也主張:如果中國不能在政府招標(biāo)中對(duì)外商一視同仁,就要對(duì)中國在歐盟的商業(yè)收購和投標(biāo)進(jìn)行報(bào)復(fù)。
在這種爭(zhēng)議中,我們固然應(yīng)該批判和警惕西方對(duì)中國的政治偏激和其他各種有色眼鏡,但是對(duì)中國企業(yè)和政府自身需要的一些策略也不應(yīng)該完全忽視反思。
威廉姆斯直言中國的海外收購在戰(zhàn)術(shù)上存在問題:“我們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感覺到,中國人買什么,什么就漲價(jià),所以戰(zhàn)術(shù)上要配套。不能當(dāng)冤大頭。”
他進(jìn)一步分析:“美國次貸危機(jī)以后,全球資產(chǎn)的水分相對(duì)被瀝干,所以現(xiàn)在這些資產(chǎn)相對(duì)來說是一種‘干貨‘,中國去抄底未嘗不可。但是抄底不等于隨隨便便直接買企業(yè),也不代表都去買美國國債。中國在進(jìn)行海外收購的時(shí)候可以注意三點(diǎn),第一個(gè)是資源類。第二個(gè)是收購人才,比如華爾街的金融人才,如證券分析師、精算師等過去要價(jià)很高,現(xiàn)在就低很多了。第三個(gè)就是繼續(xù)要和美國討價(jià)還價(jià),爭(zhēng)取引進(jìn)更多技術(shù)。”
曾幾何時(shí),富裕起來的日本人也在世界范圍內(nèi)大肆撒錢,給人留下深刻而充滿爭(zhēng)議的印象。“日本人很好認(rèn),手上拿一個(gè)相機(jī),胸前一個(gè)相機(jī),屁股上還別著一個(gè)相機(jī)”,類似嘲諷常見于1970年代的歐美媒體。從當(dāng)時(shí)很多西方影視作品里可以感受到,日本人的形象并不好,總是“有錢但是咄咄逼人”。
日本企業(yè)和政府也不落后于普通國民,收購帝國大廈,收購電影公司米高梅,整個(gè)整個(gè)地從法國購買古堡和葡萄酒農(nóng)莊等等,甚至有些日本村莊,因?yàn)榕菽?jīng)濟(jì)時(shí)期錢多花不完,干脆買入大量的黃金鑄成佛像。在泡沫經(jīng)濟(jì)破裂以后,這些“盛景”淪為后人的笑料和批評(píng)日本經(jīng)濟(jì)模式的論據(jù)。“有人說日本人玩不過美國,我倒覺得不是如此,并非日本人就沒有美國人聰明。只是日本人收購的時(shí)候還有很多經(jīng)濟(jì)泡沫,其實(shí)還是時(shí)機(jī)問題。”曾在日本做過訪問學(xué)者的威廉姆斯如此認(rèn)為。
不過從另一方面說,30年過去了,雖然日本在經(jīng)濟(jì)上依然沒有完全走出泡沫經(jīng)濟(jì)破碎后的陰影。但是其民間形象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除了老調(diào)重彈的“民眾素質(zhì)”論外,其他一些因素也依然值得考慮。
日本人追捧名牌的風(fēng)潮并不比中國人低。有人戲稱“路易斯?威登”(LV)如果沒有日本消費(fèi)者的青睞,不會(huì)有今天的地位。但是日本人自己也能創(chuàng)造牌子。川久保玲、三宅一生、山本耀司、桂由美等時(shí)裝大師早已在西方取得了不弱于其本土大師的世界影響力和地位,無印良品、優(yōu)衣庫等在西方也能受到和本土品牌同樣的追捧。
除此之外,其他日本制造也以自己的品質(zhì)打入西方市場(chǎng),贏得尊重。以威士忌為例。在2010年英國《威士忌雜志》評(píng)鑒中,最佳單一純麥品項(xiàng)由朝日啤酒的“余市”(Yoichi)奪冠;在調(diào)和式威士忌這個(gè)品項(xiàng),日本三得利公司的“響”(Hibiki)獲全球第一。在奶酪、火腿、巧克力等西方傳統(tǒng)領(lǐng)域,日本產(chǎn)品也屢獲殊榮。這值得還停留在“買和消費(fèi)”這個(gè)階段的我們思考。
通過這些具有較強(qiáng)文化屬性的產(chǎn)品,日本消費(fèi)者得以更加平等的面對(duì)西方社會(huì)而不是“頂禮膜拜”抑或“高高在上”。這點(diǎn)值得穿著Prada的衣服,開著保時(shí)捷轎車,喝著波爾多的干邑的中國買家們深思。
因?yàn)橹袊说挠^念一來洋玩意兒就是高檔貨,外國買的就是有面子上檔次,可夠顯擺,二來這幾年國貨確實(shí)不盡如人意,有的國內(nèi)的奢侈品還不如國外的普通貨
很簡(jiǎn)單,中國人好面子,認(rèn)為帶上那些奢侈品自己檔次就上來了,外國人則不這么認(rèn)為,僅僅是個(gè)偏好
因?yàn)?少數(shù)人輕易地占有了多數(shù)人的利益,
所以,他們敢于輕松地把利潤送給別人,
滿足他們那見不得人的私欲!!
因?yàn)橹袊母F人太多并且過于貧苦。中國是塊大蛋糕。中國極少數(shù)人占據(jù)著整塊蛋糕,而絕大部分只能分食蛋糕渣滓。貧富差距巨大,兩級(jí)分化落差巨大。有錢人、富人超級(jí)富裕。窮人則常常入不敷出。